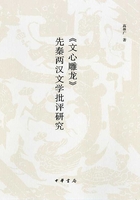
(一)周公缉颂,夫子继圣:论《诗经》的创作及成书
《文心雕龙·原道》云: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在本则论述中,刘勰谈到了周公“剬诗缉颂”、孔子“镕钧六经”,涉及了《诗经》的作者及其编次等问题。刘勰承续了《毛诗》的说法,认为周公曾经制诗作颂。《毛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龙·颂赞》云:“《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时迈》篇称颂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举,典雅醇正,因此刘勰有此评。显然,刘勰关于周公“剬诗缉颂”的提法,系采纳了传统观点。刘勰认为,周公旦多才多艺,增饰文词,制《诗》作《颂》,为后世提供了恒久的创作范式。
关于孔子之“镕钧六经”、编次《诗经》,史籍亦多有论及。《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2]《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3]这里,刘勰同样采纳了传统说法。
在《颂赞》篇中,刘勰还谈到了《鲁颂》和《商颂》的编次:“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鲁颂》因周公旦的缘故而编入《诗经》;《商颂》则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刘勰的这一认识,采自郑玄《诗谱》。《鲁颂谱》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法典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4]《商颂谱》曰:“宋大夫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唯得此五篇。”[5]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此二颂是用在宗庙里的雅乐,非宴会上的歌咏,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刘勰还谈到了吉甫作颂的问题。《才略》:“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据后人考证,《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系尹吉甫为歌颂周宣王而作。《大雅·崧高》言“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亦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故刘勰有“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之论。
关于周公制诗作颂及孔子编诗等问题,典籍虽有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堙没,已难确考,刘勰所采纳的是通常的说法。《文心雕龙》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考辨《诗经》的作者和编次者,其之所以强调突出周公和孔子,目的无非在于说明《诗经》及“六艺”乃圣人之作,值得后人去遵从和效法。刘勰是主张宗经的,在他看来,“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圣人之言,既可改造人的性灵,又是文章之奥府。刘勰之倡宗经,具有以圣人文章规范当世文坛创作的倾向,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