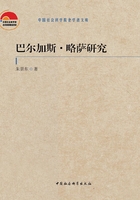
《玛伊塔的故事》(1984)
《玛伊塔的故事》(中译《犯人玛伊塔》)以叙述者描写自己开篇。他常在少年时代读书的学校附近跑步。跑步中他不由得想起一个名叫亚历杭德罗·玛伊塔的同学。他之所以想起他,因为玛伊塔也有每天跑步的习惯,他跑步是为了把自己在学校领到的一份饭送给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盲人。于是,这个慈悲善良的青年就成了小说主人公。
《玛伊塔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秘鲁,主人公是一个名叫亚历杭德罗·玛伊塔的秘鲁人,是个“革命者”,托洛茨基分子,他在秘鲁发动了一场“社会主义”革命。
玛伊塔从一个小库房里找到一些左派的报纸、加快发展和地下通告,他根据这些东西试图说服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相信,发动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刻到了。但在牢房里没有任何迹象说明要发生什么事情。不过是库房里的墙上挂着一张画着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的大胡子头像的招贴画。这张招贴画是哈辛托同志去蒙得维的亚参加一次托派组织会议带回来的。推动玛伊塔进行革命斗争的理由从他童年时代就存在着,小时候,他亲眼看到人们生活的困苦、绝望,村中存在的不公平,他应该像政治家和革命者那样做点什么,他心中总存在一种伟大的信念,信誓旦旦地总想有所作为。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也总是感到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那么多冷眼,那么多不公正,必须进行革命。
在他教母过生日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名叫巴列霍斯的现役军人,此人具有革命思想,于是二人建立了革命友谊。尽管托洛茨基党的成员们怀疑巴列霍斯扮演着泄露有关托洛茨基党的情况的情报局特工的角色,从而拒绝他参加起义,玛伊塔和巴列霍斯志同道合,决定一起在6000米高的秘鲁山区的哈乌哈小城发动一次革命。为此,巴列霍斯和玛伊塔相约前往哈乌哈做发动革命的准备工作:训练学生和农民等。玛伊塔留在哈乌哈做暴动的准备工作,巴列霍斯回利马做暴动的最后的准备工作。等他回来后革命就开始了:巴列霍斯带着一些人攻打监狱,夺取了警察局,把局长和三个警察关进了牢房。玛伊塔则带着几个人拿下了宪警队。随后他们一起奔向街头,向武装广场前进,占领了广场。然后向山区进发。就在这时,警察们进行了反扑,进山追杀他们。巴列霍斯被打死,玛伊塔被俘,关进利马第六监狱。参加暴动的那些学生也被囚禁,在监狱里关了一个月,然后被放出来交给家长看管。玛伊塔在监狱呆了10年,遇上大赦被释放。至此,玛伊塔和巴列霍斯一起鼓吹、组织和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彻底失败告终。
小说像一场闹剧,主角是无政府主义者玛伊塔和托洛茨基分子巴列霍斯,配角是五六个十六七岁的中学生,革命的发动者和参加者的思想毫无马克思主义基础,实际行动也不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更不准备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指导他们行动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其结果必然失败。正如作者所说:“我最近这部长篇小说《玛伊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拉美人对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立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证明,正像小说中的情况一样,其结果都是空想的破灭。除了某些个人的英雄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是牺牲和毁灭。”[14]
此外,小说还涉及到秘鲁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贫困,由于暴力、破坏和贫穷,整个首都就像一个大垃圾场,不难想像,主人公玛伊塔之所以从一个天主教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是因为他觉得上帝对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的不公平漠不关心。就像他对神父说的:“为什么有穷人和富人之分,神父?我们不都是上帝的孩子吗?”事实上,玛伊塔从青年时代就非常关心穷人。年轻时他曾经用不吃不喝来体察穷人的困苦生活。他总喜欢谈论穷人、人、残废人、孤儿、流落街头的疯子。他还说:“你看见利马有多少乞丐?成千上万啊!”巴列霍斯也愤愤不平地说:“世道不公平到何等地步!任何一个百万富翁的钱财都比一百万个穷人的钱还多;富人的狗吃得比山区印第安人吃得还要好,一定得改变这种不公平的世道。”于是他们就起来造反、闹革命了。
不只如此,小说还嘲讽了秘鲁的多如牛毛的革命党派:政党很多,成员却很少。更荒唐的是,这些党派之间矛盾重重,争斗不断,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不懂得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
在创作上,小说既有想像和虚构的成分,也有真实的因素。作品使用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也包括不少虚构的东西。他在1984年的一次访谈中说,《玛伊塔的故事》1962年诞生于巴黎,当时他在翻阅《世界报》时读到秘鲁山区发生了暴动,即哈乌哈的第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那是由共和国卫队巴列霍斯少尉、工会活动家哈辛托和农民领袖玛伊塔领导的。20年后,当这个事件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时候,巴尔加斯·略萨又想起它。于是他寻找发表过的有关材料,采访尚在世的人士和暴动的见证人,从而了解了发动哈乌哈暴动的主要人物的情况。然后他又了解暴动的背景,知道暴动是在利马的一次节日期间酝酿的。关于暴动的背景的报道材料就成为小说的基础,作者又发挥其想象力,设想了若干历史事件,一个完整的故事便形成了。
在结构上,小说不乏独特之处。全书分为10章,为讲述作品的故事,作者做了这样的安排:每一章都以采访玛伊塔的某位亲朋好友或同志或他本人等入手,各章则分别从主人公的童年、少年、青年、老年、党内生活、社交活动、家庭生活、武装暴动的策划、发生及结局等角度刻画人物,并且将对话与独白、交谈与叙述、过去与现在、此地与彼地等突兀地穿插在一起,像电影镜头那样转换、跳跃,从而扩大了表现的时间和空间,把一切时间、地点、人物与事件都置于眼前,不做任何过渡性的说明。比如第三章,讲述现在“我”驾车去采访修女华尼塔和玛丽亚,以及了解玛伊塔的情况。华尼塔刚变到她弟弟和玛伊塔是好友,对他弟弟影响很大,便突然跳到过去,讲述玛伊塔跟陆军少尉的谈话:谈到他们如何占领了那个村庄,攻下警察局,打开监狱……他们可以骑马、骑驴、坐卡车、步行进山。明天去哈乌哈。还谈到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然后又跳回华尼塔的谈话,说玛伊塔比他的实际年龄大,差不多都40岁了呢,像个50岁的人。这一章就这样跳来跳去,交替描述华尼塔、玛丽亚、玛伊塔、巴列霍斯和神父之间的谈话、有关问题,跳跃多达几十次。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者声音有时和主人公的声音及作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叙述者通过和不同的革命同志的交谈获得了各种信息,后来玛伊塔和他们一起建立了一个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从而开始面对那些年间他们所怀抱的革命理想。对玛伊塔的描写从一开始就很具体,只是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增加了不多的典型材料。在叙述者讲述故事的一切场合时,他没有忘记描写街道、住宅、人物及其感受、感觉和激情,总是把他们25年前的情形和会见时的情形相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一开篇作者就把读者置于利马市的一处海滩上,描写得那么详尽而准确,让人很容易想象那是什么地方,感觉到环境的潮湿,甚至闻到海水的味道和随处可见的垃圾的臭味。随即让小说的主要人物玛伊塔现身,他是作者的老同学。玛伊塔是一个极其热情的人,他的为人似乎注定会使他成为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者。
《玛伊塔的故事》虽然已出版30余年,但是它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对待。对此,巴尔加斯·略萨深感遗憾。他说:“无疑,我这部小说受到最糟糕的阅读。令我吃惊的是,我受到的许多攻击是人物的同性恋。由此我发现,那些年秘鲁的左派非常可恨,他们具有一种惯常归咎于保守阶层的偏见:他们认为把玛伊塔写成同性恋者,这太丑陋了。人们是作为一种反对左派的小说来读的,因为是一种尖锐批评左派的立场,但是实际上,这是一部关于一个悲剧人物的小说。那些年间,拉丁美洲的左派,不只是秘鲁的左派,都很狂热,很教条,令人不能容忍。”[15]
巴尔加斯·略萨具体地谈到过创作此作的过程、背景和如何为写作做准备的情况:“暴力是我新近出版的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我的其他小说一样,这部新作写出来后和我开始写的十分不同。在写它的过程中,主题是逐渐确定的,具体化的,并且呈现出一系列推测、推论和可能性,直到小说结束、我有了判断的基础,一切才清楚。
“和其他可以根据一种虚构、一种想象、一种幻想、一种梦幻写作的作家不同,我往往以我直接感受到的具体经验或间接听到或读到的事情为基础来写作。这种从具体现实、从亲身经历出发的做法,实际上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件事、一个人物使我受到鼓舞,推动我写作。至于《玛伊塔的故事》,出发点是1962年我在巴黎的一份报上读到一则简讯,当时我住在巴黎。我在《世界报》上看到一则被淹没在许多外国新闻中的关于我国的消息。消息说在一个中心城市即哈乌哈有人发动起义,起义几个小时后就被镇压下去,造成了一些伤亡。
“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激动。那些年间,我和许多拉美国家一样,怀有革命的幻想和热情。从古巴革命获得胜利起,革命是可能的想法就在美洲的空中飘荡。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古巴已经证明这是解决拉美问题的唯一道路。从零开始,通过英勇的暴力行动完全打破旧社会,建立一个新社会、一个平等的社会,正义和自由这些字眼儿才真正有意义。突然在报上看到在我自己的国家发生了持续几个小时的革命,令我异常激动。《世界报》上的消息激发的那种想象,萦绕在我的脑海,最终成为小说的萌芽,产生了一些形象,想象开始围绕这些形象活动,慢慢出现了一些趣闻轶事和可能的叙述线索。
“那时,巴黎是拉丁美洲革命的交叉路口,拉美国家的许多青年经过巴黎去古巴或离开古巴。当时古巴受到严厉封锁,拉美国家同古巴早就断了关系。这使我们这些生活在巴黎的拉美人和来自不同的拉美国家的革命者有了密切接触。他们在我们中间保持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的乌托邦思想。在来往的人士中,自然有许多秘鲁人。一天夜里在巴黎一条街上,和一位秘鲁人交谈时,突然提到了哈乌哈那段历史,那个不祥的故事。和我交谈的那个青年曾在利马监狱里蹲过几个星期,他在狱中认识一个曾参加哈乌哈那场革命的人。他对我讲述了那段历史。他对我说,一个年迈的托洛茨基党员熟悉四五十年代的所有左派团体和组织,在和马苏基利奥区一次节庆活动中他突然对一个跳华尔兹和马里内拉舞的小青年谈起社会主义革命来,他说有可能进行革命,秘鲁只缺一批有决心的人,因为秘鲁的印刷条件绝对适合进行一场这样的革命,此外还因为从殖民时代起秘鲁就有起义、打游击的传统,这种传统在这样的农民中存在着发扬的可能性,他们曾在图帕克·阿马鲁革命或普马塔瓦革命中进行战斗。他说话的热情很高,信心很足,开始跟他交谈起来。那个年幼无知的孩子谈论他一生致力的事情时的天真、纯朴和冷静一定使他感到很高兴。那个孩子不可能怀疑为了进行革命上山打几枪会有问题,问题是长期的耐心,就是说,那位老人在漫长的20年30年间所从事的谨慎、勤劳、艰苦的地下活动。在交谈过程中,年迈的托洛茨基分子突然发现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人是军队的一名少尉。他感到非常吃惊。他向所属的组织报告说,他同少尉进行了接触。组织建议他跟少尉保持联系。他们觉得跟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一个人建立联系很重要,那是一个拥有武装力量、有训练的世界。也许可以吸收他。于是,在很有经验的老地下革命者和天真的、从没有从事过政治活动、出于激情、感觉和想象谈论革命的少尉之间便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认为是老托洛茨基党员想为他的事业争取这个年轻人。但是发生的情况相反:没能力经验、不负责、感情用事的青年人竟然诱惑他,为他的事业、为一次在中部山区一个镇子准备的革命争取他。
“当那个秘鲁青年在巴黎对我讲述那个故事时,我被那种角色突然调换的关系吸引住了。那个年迈的有经验的老人把那么多年的战斗经验全都抛开,一下子跳起来,一点儿也不冷静,发疯了似的,仿佛手里拿着一支步枪,开了一枪,扔了一只炸弹,年轻的少尉准备的革命爆发了一样。这件事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鼓舞人心,我那么坚信不疑,从那时起便产生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
“但是过了很久我才动笔。我在写别的作品。《玛伊塔的故事》,可以叫它《年迈的托洛茨基党员》,一直在我的头脑中,有时会消失,不久又复回,用我遇到的事、有关的事、我听到的事,使故事变得复杂的事丰富它。与此同时,在我国和拉美其他地方不断发生许多事情。出现了新的起义尝试,有的不理智,有的很短暂,有的不像哈乌哈的起义那么短命。在60年代的秘鲁,至少有4次这样的革命尝试。参加尝试的所有人中,有一些我认识,甚至有我的朋友,在欧洲一块生活过。当然这一切给我留下了关于作为最后解决办法的革命暴力的越来越不清白、不纯洁的印象。当然这一切为写《玛伊塔的故事》提供了营养。
“当我决定写这部小说时,我首先要做的是围绕主题进行一次调查,真正搞清楚哈乌哈的冒险是怎么回事。已经过去了20年,这肯定有利于为小说的主人公和历史的见证人找到真正的文献。我首先调查主人公,寻找幸存的人,说服他们对我讲述他们知道的情况。同时我开始嘴馋资料馆,翻阅那个时代的报刊,看看国家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事件是怎样发生的,新闻界、政党是如何评论的。于是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我得到的关于发生的事情的说法不但没有澄清事实,反而弄得更混乱了,那些说法都非常矛盾。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很有趣,对我来说也许比故事还有趣,因为在一些情况下,记忆对见证人、对主人公不忠实,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记忆的变化是随意的,它服从验正某种态度的需要,或者只是证明角度的变化、视点的变化的需要。于是就把那件小事、开始似乎完全清楚和明确的小事件变成了某种十分有伸缩性、复杂而多变的东西,某种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观察和描写的时间来看,十分不同的东西。这样,我觉得除了我一开始想讲的故事,我还应该讲述这个次要的故事,就是已经变得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已经变成恰恰从30年前我就致力于写的东西:一部虚构的小说。把那个事件变成一部小说的方式恰恰就是把材料变成小说的方式。”[16]
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托雷斯—古铁雷斯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中肯的:
“巴尔加斯·略萨的《玛伊塔的故事》这部小说远远超出了对秘鲁本世纪中期的一次革命的讲述。显然,它吸引读者的首先是主题,是富有激情的、充满事件的故事。正是这一点,说明巴尔加斯·略萨是一位大师:他使小说首先是故事,是事件……然后是语言。但是在小说中,他突然一跳,将奇闻轶事和时间、不同时代的对话、在另外的背景下的话语,或叙述故事的意识结合在一起,显示了巴尔加斯·略萨叙述形式的不拘一格和娴熟。
“小说的故事大部分发生在利马这个可怕的城市。小说人物在一个丑陋和老掉牙的城市里东奔西走,对拉丁美洲人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进行革命尝试的时代。小说的其他部分的故事发生在秘鲁安第斯山地区:那是从城市通向农村的道路,拉丁美洲大多数革命工人党选择的战略要道。
“这是关于这个事件写的最离奇的冒险,但是也为许多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看到了小说讽刺地反映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在小说中,语言留给读者一股酸苦的味道,也使之感到仿佛亲自参加了那番不寻常的英雄行动。我们和玛伊塔一起行走,和他坐在一起,和阿纳托利奥及巴列霍斯坐在一起,他们的雄心吸引着我们,他们那‘质的飞跃’的思考和思想吸引着我们。”
“小说也是托洛茨基主义革命工人党的故事,或者说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勇于创建一个政党的团体的尝试的故事。《玛伊塔的故事》是对一个人(托洛茨基分子)的嘲讽,他根据一个小库房里装满的左派报纸、通告和地下书籍试图说服‘中央委员会’的七个人相信,去农村发动革命的时刻到了。”
“凭借小镇哈乌哈监狱的领导者、一个20 多岁的少尉想出来的星火燎原的计划,玛伊塔找到了发动一次‘真正的革命’的机会。玛伊塔的生活总是充满一个边缘人物的矛盾: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同性恋’,他知道他的婚姻、他的父亲地位和他作为属于一个多次分裂的托洛茨基党的政治家的前程都面临着危机,于是他试图在几乎不存在的哈乌哈小镇依靠一帮不像革命者而更像童子军的孩子进行冒险,试图夺取政权以改变现状。其企图自然荒唐可笑。”
“小说犹如那个时代的左派团体的一幅杰出的壁画。政党内部的争论、阐述内部矛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式,如何区分共产党、毛派分子、托洛茨基分子的方式,构成了几乎在30年间拉丁美洲的左派的状况的全貌。”
“显然,小说对拉丁美洲的革命左派特别是托洛茨基党派进行了‘准确的批评’。但是毫无疑问,同时也再现了一个几乎和古巴革命同期发生的事件。”
“可以肯定的是,小说包含着一些后现代的叙述特征:时空的汇合、对话的交织、不明确的表述、叙述的自觉意识、广征博引、作为结构成分的文学评论、历史的碎片、时代和人物的同时性、有意识地讲述失败和绝望的故事等。”
“自始至终,读者都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叙述者即作者本人,他一心致力于搜集写小说需要的材料,叙述者在向读者讲述写作工作。”
“小说的叙述者——作家一面为写玛伊塔的故事而重访他去的地方、采访和他一起冒险的战友、核实关于运动的看法,一面深入了解秘鲁当前的形势,为写小说做准备。”
“小说也是一种训练,不是为了深入思考他的想法,秘鲁不在于此,而在于形式。这部小说就像盖一幢大楼,不隐藏它的建筑材料,就像我们看到的那些现代楼房,有管道系统,紧挨着许多楼层的拐角。作家收集写小说的材料(这项工作没有顺序,因为一次采访接着一次采访),与此同时,他讲述了他对文学的担心,发表关于时政的看法,让玛伊塔讲话,让他当年的战友发表意见,进行争论,由他们自己构建故事。读这部小说如同查一趟作家写作和思考的路线,或者说,如同作家沿着玛伊塔的脚步前行。”
“但是,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结尾。巴尔加斯·略萨致力于寻找真正的玛伊塔的任务,找到的却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找到他,把他带到他的办公室交谈,而且把这件事讲给读者听。读者终于明白,利马的玛伊塔是一个不幸的、绝望的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