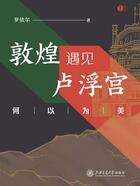
1 卢浮宫有股路易十四的味道
用最实用主义的眼光来看莫高窟和卢浮宫,可能都是一张门票的形状。
如今,无论到博物馆、美术馆或是什么景点,我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参观时的体验。卢浮宫每年的参观人数从20世纪90年代的500多万涨到近几年的一千多万,蝉联“最受欢迎博物馆”的宝座。而随着近几年的热潮,莫高窟的游客人数几乎达到了洞窟能承受的峰值。

▲莫高窟参观人数增长幅度大,这与敦煌在各地的巡展与大量相关电视节目有关。

▲阿波罗画廊
漫步在卢浮宫内,天光洒进巨大的石头建筑。讲真的,任何东西展示在这样的圣殿都会让人肃然起敬。踱步于似乎过于金碧辉煌的阿波罗画廊(Galerie d'Apollon),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头顶假发的路易十四。画廊建造的时候(1665—1670年),路易十四刚刚决定了把太阳视为自己的象征物。作为国王的第一个皇家画廊,阿波罗画廊可以被视作日后凡尔赛宫的先行版。要解释天顶上那些阿波罗相关的神话故事可能要花很久,但千言万语可以汇成4个字:君权神授。踏入宫殿的朝圣者必须被君主的权威所震慑,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用宏大的建筑与华丽的雕塑来吓人,这可能也是所有皇宫建筑的逻辑。

两者都有高高在上的感觉
▲路易十四画像
“哇,不愧是太阳王,阿波罗画廊里亮得好像每时每刻都在被艳阳灼烧。”
“哇,不愧是太阳王,假发、白丝、高跟鞋,把自己打扮成一栋巴比伦式的宫殿(亦略像贵宾犬)。”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欧洲旅游时连看三天皇宫后,就恨不得盯着宋徽宗的汝瓷看一会儿,它能中和我们被巴洛克“摧残”的视觉。同理,在纽约那些当代美术馆的“白盒子(white box)”里待三天,也会让人变得太过阳春白雪、难交朋友。

▲凡尔赛镜宫

▲北宋汝窑青瓷胆瓶
如今,卢浮宫里早就不住国王了,艺术博物馆一直是最宽容、民主的机构,认真地对待各种文明的藏品、每一类少数人群。但我们依然可以随时体验到中世纪圣迹巡礼般的宗教狂热:在拿破仑三世的国务厅(Salle des États)中,这位法国末代皇帝的强国梦和他那金光闪闪的装饰早就成了历史的尘埃,只剩下“那位女皇”(蒙娜丽莎)正在接见芸芸众生。身处艺术的“圣像”前,每个人都成了当代的“十字军”,无论是被挤成“呐喊”模样的扭捏状,还是钱包被顺,这世上还有比为艺术受难更高雅的事情吗?我们在蒙娜丽莎真身前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人生中最精彩的酒后段子。身处真正的稀缺资源前,我们很难感觉到那“引领人们的自由”。

《蒙娜丽莎》所在地国务厅以前有华丽的装饰,现在有糟糕的体验。

▲《自由领导人民》,欧仁·德拉克罗瓦,1830年

▲《迦拿的婚礼》,保罗·委罗内塞,1563年
在艺术“圣像”面前,展厅内所有的画作都成了“蒙娜丽莎的弄臣”“偶像团体的后排”,就连她正对面那幅委罗内塞的杰作《迦拿的婚礼》都难以幸免。画家不愧沿袭了文艺复兴时期全欧洲最商业、最风流的威尼斯的风格,10米长的画面上塞满了衣着华丽的各国人士,连中间的耶稣与其母亲都显得没那么突出。“神之子”就这样冷漠地看着画中的俗世,看着画外背对着他的我们。耶稣的正上方竟然有人拿着菜刀在切肉,对面有新救世主:蒙娜丽莎不但能经历被盗之难后复活,而且降临任何国家都能造就展览史上的奇迹,卢浮宫里这块500年前的木版(油画)成了神圣且无价的偶像。在《迦拿的婚礼》中,耶稣把水变成了酒,与此同时,达·芬奇500年前创作的同样以耶稣为题的《救世主》则卖了约30亿人民币。
卢浮宫的国务厅是当今博物馆现状的最佳隐喻:在宗教和皇权示弱的今天,艺术正慢慢成为新的信仰,填补人们心灵的空缺。昔日宏伟专权的皇宫成了每个人的世俗教堂,馆内来自世界各地的藏品越多、越集中,就越受大家欢迎。大都市中心的大博物馆门庭若市,而你若是走进小博物馆,则几乎可以享受“包场待遇”。

▲《迦拿的婚礼》前站满了排队看《蒙娜丽莎》的参观者

▲肯尼迪曾为《蒙娜丽莎》到美国巡展致辞

▲《救世主》达·芬奇 约1500年
卢浮宫从兴建至今已历经800余年,虽然如今的它成了博物馆,但宫廷建筑的本质依然没变。
而在世界的另一头,位于中国甘肃省的莫高窟,大多数洞窟是与你我同样的民间人士所造,它与博物馆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画中的耶稣在人群中面无表情地“看”着对面的《蒙娜丽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