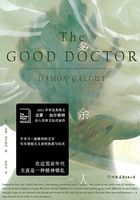
第3章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就想:他在这里待不长的。
傍晚我正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门口,单手提着行李包,穿着普通:牛仔裤、褐色衬衫,外面罩着白大褂。他看上去很年轻,茫然中带着些许不知所措,但这不是我认为他待不长的原因。我看出他脸上有着别的什么东西。
他说:“您好……这里是医院吗?”
他又高又瘦,声音却出乎我的意料,听上去很低沉。
“进来,”我说,“先把包放下吧。”
他走了进来,但并没有放下行李。他紧紧抱着它,环顾办公室四周的粉红墙壁、空椅子、墙角里沾满灰尘的一张书桌、花盆里枯萎的羸弱植物。我看得出来,他觉得一定是来错了地方。我很同情他。
“我叫弗兰克·埃洛夫。”我说。
“我是劳伦斯·沃特斯。”
“我知道。”
“您知道?”
他似乎很惊讶我们竟然一直在等他,尽管他最近几天总是给我们发传真,宣告他的到来。
“我们会住在一起,”我对他说,“我带你去看看吧。”
宿舍在一座单独的厢房内,我们需要穿过停车场附近的一片空地才能到达。刚才他过来时,一定曾踏上过这条必经之路。然而现在的他望着这条蔓草丛生的小路,头顶上方参差不齐的树木正掉下层层落叶,他露出一副刚刚觉察到这一切的神情。
我们顺着长长的小道来到了房间。时至今日我一直独居于此。两张床、一个橱柜、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一幅画和一面镜子,屋里还有一张绿色沙发、一张合成木制矮茶几、一盏灯。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配置,隔壁几间住了人的房间看上去也一模一样,一如某些平淡乏味的旅馆,唯一可显出不同的是各自房间家具的摆放位置。两天前,他们搬进来一张新床,此外我房内从来没有费心移动过任何东西,也从未添置过新的家具。这些难看、简陋的家具没有任何风格,在这片中性的背景中,哪怕只是多了一块布的点缀,也能透露出寓客的些许个性。
“你可以睡那张床,”我对他说,“橱柜里还有放东西的地方。浴室在那扇门背后。”
“噢,可以。好的。”但他还没有放下行李。
两周前我才听说有人要来和我同住,是恩格玛医生把我叫过去告诉我的。我不太情愿,但也没拒绝。在随后的几天我虽有抵触,但还是接受了合住的想法。也许没有那么糟糕。我们可能会和睦相处,有个同伴或许是好事,我的生活也许会有好转。或多或少地,我开始充满好奇地期待这种变化。在他到来之前,我做了一些小事来欢迎他。我把新床安放在窗下,铺上了洁净的床单,清空了橱柜里的几个架子。我甚至还破天荒地打扫了地面,清理了房间。
而现在,他就站在我面前,透过他的眼睛,我能觉察到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房间很丑,空荡荡的。劳伦斯·沃特斯看上去并不是我脑海里想象的那个人。我不知道我到底想到了什么,但绝不是这个平淡无奇、浅褐肤色的小伙子。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男孩。他终于放下了行李。
他摘下眼镜,在袖子上擦拭了几下后,又戴上了。他无精打采地说道:“我不懂。”
“什么?”
“这个地方。”
“医院?”
“不仅是医院。我是说……”他挥动着一只手,指向外面的世界。他说的是医院围墙外的城镇。
“是你主动要求来这里的。”
“但我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这样?”他突然情绪激昂地说,“我搞不懂。”
“我们下次可以好好谈谈。但现在我还在值班,要回办公室。”
“我一定要见恩格玛医生,”他突然说道,“她在等我呢。”
“现在不要担心这个事情。你可以明天早上去,不着急。”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随便什么都可以。收拾行李,熟悉一下新环境。你也可以来和我一起坐班,再过几小时我就下班了。”
我让他一个人待着,自己先回到了办公室。他感到震惊,心情沮丧。我感同身受,初来乍到的时候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你满怀希望而来,现实却呈现给你完全不同的东西。
你期盼能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城镇,镇里有一家繁忙的现代医院,它也许坐落在农村,规模不大,但是充满活力。这里曾是某个黑人家园的首都,所以无论其诞生背后的政治道德如何,你都会期待一个管理完善、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当你驶出前往边境的主道,一路沿着通向此地的小公路入城的时候,这个小镇依然貌似和你期待的没有多大出入——如果从远处遥望的话。镇里有一条主街,通往喷泉和塑像坐落的镇中心,通向店面、人行道与路灯,还有坐落在更远处的房子。它看起来干净整洁,规划有序而精准。你来到了一个像样的地方。
然后你到了镇里,看到了周围的现状。第一个让你起疑的线索可能是一处令人不安的细节:一条裂缝贯穿了一面本来崭新的墙,或是你开车经过一栋有几扇破碎窗户的办公楼,或许是干涸的喷泉,泉池里积满了陈沙。你缓缓驶过,带着隐隐的焦虑四下观望,突然一切都变得分外清晰。人行道和砖块接缝处的杂草,街道上四处丛生的野草,灯泡炸裂的路灯,光溜溜的玻璃门后沉睡着的空荡商店,发霉、潮湿及起泡的刷漆墙面,雨痕斑驳的墙壁。房屋正在缓缓坍塌,碎片时而一粒一粒,时而一片一片地往下坠落。此时你已不再确定自己到底身处何方。
街上空无一人。这是你最后才注意到的一个景象,尽管此刻你意识到这是给你带来不安和空虚感的最初原因:这是一座空城。没错,是有一辆车在巷陌徐徐行驶,一两位身着制服的人在人行道上闲逛,也许会看到一个身影垂头丧气地走在小径上,穿过一片荒草连天的空地,但大多数时候这镇上几乎是空的。四下无人。没有人声,没有人迹。
一座鬼镇。
“这里看上去好像发生过可怕的事情,”劳伦斯说,“它给人的就是这种感觉。”
“哦,但事实正好相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这才是问题所在。”
“那怎么……”
“什么怎么?”
“没事。只是想知道怎么回事。”
他的意思是:这个镇子到底是怎么出现在这里的?而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不是一座由于正常的人类活动而自然形成的城镇,如干旱地区的一条河流,或发现了金矿,或某些历史事件。这是一座空中楼阁式的城镇,是由贪官们在纸面上构想和规划的,而他们居住在城市里,远在天边,甚至从未踏足过这里。他们在地图上画了一个轮廓并说道:这是我们的黑人家园,首都应该在哪里呢?为什么不放在这里,在中间?他们用红笔画了个叉号,所有人都沾沾自喜,然后派人找政府建筑师来制定规划。
所以劳伦斯的困惑并不稀奇。我自己也经历过。我知道这种感觉都会过去的。一两周后困惑会被其他东西代替:也许是失望,或是怨恨、愤怒。然后这种心情会转变为无奈认命。短短数月后,劳伦斯或者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在这里强忍着他的谪居刑期,或者会谋划一条出逃之路。
“但他们都在哪里呢?”他问我的样子更像是在问天花板。
“谁?”
“人啊。”
“就在镇外面,”我说,“他们住在那里。”
这是数小时后的当夜,在我的房间——不,我们的房间里,我刚熄灭了灯,躺在床上,想要入睡时,他的声音从幽暗中传了过来。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住在那里?为什么不住在这里?”
“这里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的?”
“什么都可以啊。当我开车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乡下的情况。那里一无所有。没有旅馆、商店、饭店、电影院……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不需要这些。”
“那医院呢?他们难道不要看病吗?”
我一只肘撑着床坐了起来。他在抽烟,我能看到红色光点起起伏伏。他背贴床,脸朝天。
“劳伦斯,”我说道,“要谨记一件事——这不是真正的医院,而是个笑话。你开车过来的时候,还记得路过的最后一个小镇吗,离这里一小时的那个?真正的医院在那儿。那是病人去的地方。他们不会来我们这儿,这里什么也没有。你来错地方了。”
“我不信。”
“你还是相信为好。”
红光一动不动地在空中停了片刻,然后又升起、下落、升起、下落。
“但人会受伤,会生病。他们难道不需要帮助吗?”
“你知道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是以前军队起家的地方,他们的傀儡独裁头目曾住在这里。他们厌恶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政治,”他接着我的话说,“但那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已不再重要了。”
“过去才刚刚发生,它还没有远离我们。”
“我不管那些事情。我是名医生。”
我躺下了,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几分钟后他把烟头碾在窗台上掐灭,扔出了窗外。他嘟哝了一两个我听不清楚的词,双手做了个手势,叹了口气,就入睡了。这几乎是一瞬间的事,他累蔫了,我能听到他均匀的呼吸声。
我却无法入眠。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他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夜了。这情景让我想起多年以前,曾有过一段时间,当我憧憬着有人在黑暗中依偎在我身旁、伴我共眠的画面时,我会感到一阵阵慰藉与安逸,觉得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了。这些回忆几乎与今晚格格不入,因为他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现在,这具会呼吸的身体让我感到紧张、警惕、有些愤怒,所以我一直睡不着,直到数小时后才累得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