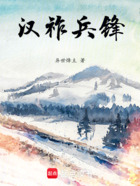
第28章 质子刘协
杏贞裹着狐裘踏入十常侍的密窖,张让正用朱砂篡改竹简。
“云中郡的‘急报’还缺个信物。”
她摘下刘协的长命锁,狠心斩断一缕胎发,
“王玢儿子的小指,可仿得像?”
张让的银刀挑开蜡封:
“贵妃娘娘,这断指若用羌奴的,血渍怕不对。”
“用鲜卑战俘的。”
杏贞将胎发缠上断指,
“慕容廆送来的三百活口,不正是为此?”
地窖深处传来凄嚎,杏贞抚过冰鉴中的玉玺拓本:
“告诉慕容廆,他的‘白狼骑’该在朔方现身了。”
永康殿的青铜兽炉吐出袅袅檀烟,却压不住灵帝额角的冷汗。
杏贞的指甲掐进掌心,面上却浮着悲悯:
“昨夜紫微垣动摇,张常侍说……说白狼星已抵天关。”
她话音未落,殿外忽起骚动。
十常侍张让捧着一卷染血的羊皮闯入,身后跟着个浑身血污的驿卒。
“云中八百里加急!鲜卑焚毁武泉驿,太守王玢殉国!”
张让的尖嗓刺破死寂。
他抖开羊皮,赫然露出半截孩童断指——那是王玢幼子,指节上还缠着灵帝亲赐的五色长命缕。
(《风俗通义》端午习俗表示皇权与巫蛊的结合体)
杏贞的鲛绡帕适时落在断指上,遮住灵帝发颤的指尖。(《博物志》“鲛人织绡“暗示杏贞双重身份(汉妃/胡裔))
“陛下可记得元狩四年的旧事?”
她将《太史公书》翻至勾连处,
“霍骠骑封狼居胥,方得漠南无王庭。今若使协儿......”
“贵妃是要朕的骨肉祭天?”
灵帝猛地掀翻案几,龟甲筮草散落满地。
杏贞顺势跪在碎陶片上,殷红自素纱襦裙渗出,恰似当年吕布为她挡箭时的血花。
“臣妾愿随协儿北狩!”
她仰起脖颈,露出匈奴女子特有的修长曲线,
“慕容廆歃血为誓,只要皇子在龙城一日,鲜卑绝不南下半步。”
铜壶滴漏声里,灵帝的目光扫过殿角鎏金铜驼——那是他初登基时熔铸的祥瑞,如今驼首已生绿锈。
杏贞知道,帝王心防裂了。
吕布解下兽首吞肩铠时,一枚狼牙坠从护心镜后滑落。
二十年了,獠牙尖端的血沁早已发黑,却比今夜月色更灼人。
吕布的指腹无意识摩挲着左肩甲胄——那里藏着杏贞亲手缝制的十二章纹残片。
三年前那个雨夜,贵妃剪下灵帝衮服上的日月山纹时,指尖曾划过他锁骨旧疤:
“当年鲜卑狼骑踏破九原,可想过今日能披天子图谶?”
记忆如赤兔扬蹄般撞开尘封往事。
张让捧着伪造的《并州勋册》宣读“阵斩鲜卑裨王三人”时,
皇甫嵩的冷笑刺穿德阳殿:“卫青十八为侍中,吕奉先廿九领狼骑,贵妃用兵之道,倒是比孝武皇后更胜一筹!”
那日他甲缝里还沾着并州沙尘,十二冕旒后的灵帝却始终闭目如泥塑。
“将军,永巷第三棵槐树。”
传信的哑婢比划完便吞金自尽。
吕布抚过戟刃上九道狼头纹——那是杏贞及笄那年,他猎杀头狼所刻。
子时的梆子刚响,赤兔马已踏碎永巷青砖。
杏贞褪去九翟冠,散着发靠在槐树干上,腕间金跳脱叮当,恍若当年并州牧羊女。
“他们要杀协儿。”
她将虎符按进吕布掌心,冰凉触感激得他战栗,
“十常侍在玄铁马车夹层灌了水银,行至白道城便会车裂。”
吕布的戟尖挑起杏贞下颚:“某若不应?”
宫墙外忽然传来铁甲铿锵,杏贞轻笑:
“西园新军正在围剿袁隗府邸,听说袁太傅私藏了一把鱼肠剑。”
她指尖划过戟杆旧伤,“就像建宁元年那晚,你救我时中的那一箭。”
吕布瞥见杏贞袖中滑落的竹片——那是蔡邕昨日进呈的《琴操》残篇,朱批“江都公主”四字旁,竟有孩童用炭笔勾勒的瑟弦纹。
“蔡中郎那女娃娃倒有胆色,”
杏贞轻笑,“八岁稚童,竟识得未央宫旧谱的商声变调。”
赤兔马突然人立而起,吕布这才发现槐树皮上钉着半支鸣镝——与当年鲜卑射伤杏贞的箭一模一样。
吕布的拇指无意识摩挲戟杆凹痕——那是建宁元年的箭伤。
彼时杏贞刚入宫,他单骑劫囚车,却被鲜卑神射手郁筑鞬一箭贯穿肩胛。
“走啊!”
杏贞撕破宫装为他包扎,“你若死在此处,谁替我杀尽天下负心人!”
十七岁的吕布啐出血沫:“等我当上将军,用慕容廆的头骨给你做妆奁!”
赤兔马突然喷着响鼻,将吕布从回忆中拽回。
他抚过马颈那道月牙状伤疤——三年前杏贞赠马时,这匹缴自羌渠单于的汗血驹,还戴着慕容部进贡的黄金辔头。
“此马名唤赤兔,日行千里,夜渡冰河。”
杏贞亲手卸下辔头,将缰绳绕在吕布腕间,
“单于帐前连折我九名汉使才夺来,你可莫辜负它的烈性。”
吕布至今记得,赤兔初入洛阳那夜踢死了三名西园马奴。
杏贞却立在血泊中轻笑:“果然只有奉先的戟,镇得住这饮过天山水的神骏。”
马厩的火把在她眼中跃动,恍若并州野火。
而今那支鸣镝就钉在眼前,箭簇上的狼图腾与郁筑鞬的一模一样。
吕布突然暴喝,画戟斩断槐树:“慕容老狗竟还活着?!”
二十年光阴在这一箭里坍缩成团,他哑声问:“何时启程?”
五更鼓响,德阳殿的蟠螭灯映得蔡邕须发皆赤。
蔡邕须发戟张,高举褪色的青简:
“《白虎通·藩臣篇》明载'四夷虽大,皆属汉臣'!”(原型班固《白虎通义》卷六用意为和亲政策提供经学依据)
残缺的简牍上,“单于岁贡”的朱批赫然在目,与杏贞手中篡改过的绢帛本形成刺目对比。
“啪!”
张让甩出的玉笏在蔡邕额角绽出血花,十二冕旒后的灵帝闭目不语。
杏贞垂帘轻咳,赵忠立即捧出个漆盒,盒中竟是块生满蛆虫的带骨羊肉。
“此乃慕容廆所献蹛林宴胙肉。”(匈奴秋祭(《史记·匈奴传》)表示鲜卑汉化进程中的文化杂糅)
杏贞的护甲叩响金帘,
“太尉可知,鲜卑以战马肥瘦占吉凶?马瘦则南下牧马,马肥则——”
她突然掀帘直视蔡邕,“饮马黄河!”
殿外适时传来马嘶,三百并州狼骑甲胄染霜,方天画戟映着朝阳,在白玉阶上投下森森戟影。
吕布策马踏过丹陛,马蹄铁在御道上擦出火星,惊得百官扑簌跪地。
“三日後寅时,皇子銮驾出朱雀阙。”
杏贞的护甲划过舆图,在幽州处剐出裂痕,“吕将军,莫忘白登山旧约。”
西园校尉踹开蔡府时,蔡邕正焚烧书简。
“《汉书》注疏岂能落入阉竖之手!”
老仆将最后几卷塞入枯井,却被禁军拽着发髻拖出。
杏贞的贴身宫女阿箬拾起未燃尽的残片,尖声笑道:
“蔡中郎好胆量!竟敢篡改《匈奴传》!”
残片上赫然有杏贞朱批:“江都公主句删之。”
未完工的桐木琴胚在禁军刀下裂成两半,第七根丝弦崩开,在蔡邕指腹勒出血痕。
阿箬碾着散落的琴轸:“贵妃娘娘说,今日裂的是木胎,明日......”
八岁的蔡琰蜷在父亲广袖下,攥紧未编完的竹简目录册,虫鸟状的速记符号在她掌心印出红痕。
蔡邕还要争辩,却见自己的女儿蔡琰被禁军押至殿角。
刘协的玄铁马车驶过北邙山时,最后一片槐叶正落在他掌心。
玄铁马车内壁刻满划痕,是历代和亲公主的绝命诗。
刘协的乳牙咬住暗格铜环,借全身重量坠开机关,暗格弹开瞬间,霉味混着龙涎香扑面。
一卷泛黄《西域图志》里夹着杏贞手札:
“元初五年,班勇以三十六人定车师。吾儿若惧,当观此卷。”
(原型班勇《西域风土记》用意暗示杏贞与西域都护的隐秘联系)
羊皮地图上朱砂勾连,标注着慕容部水脉与粮仓。
车外忽传马嘶,刘协匆忙吞下药丸。
苦涩漫开时,他摸到图志封底的小字:
“霍去病十九封侯,陆昭廿一镇北。协儿,你已四岁了。”
车外忽起鹰笛声,与杏贞教他的匈奴小调一模一样。
他摸索着窗棂暗格,果然触到个油纸包。
“协儿,若见狼头纛,便服此丹。”
母妃的字迹被水渍晕开,想来是垂泪写就。
纸包内除了蜡封药丸,还有枚生锈的箭簇——正是当年吕布所中那支。
铜雀台的晚风卷起灰烬,杏贞凝视未燃尽的“河汾”二字。
“娘娘为何不留个念想?”阿箬欲捡残片,却被一脚踹开。
“并州的月,洛阳的井,都照不亮这盘棋。”
她将灰烬撒入洛水,
“告诉张让,该给辩儿下‘鸠毒’了。”
残月映出她袖中另一封血书,那是刘协用药汁写的:
“母妃,儿见慕容廆帐中有金狼头冠,与父皇的冕旒一样高。”
《后汉书・献帝纪》注引《幽州杂记》:
“帝尝示陆昭断箭,叹曰:‘此非鲜卑镝,实母妃心。’昭默然,以指叩箭簇,其声如泣。”
那支箭最终插在了白狼山祭坛上,与霍去病的祭天金人并肩而立。
只是无人知晓,金人足底刻着杏贞的小字:
“中平二年春,杏贞观兵于此。”
其时去孝武皇帝封禅,已隔三百二十秋。
ps:
太宗御批
(掷狼毫于奏疏,墨溅《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
一、破胡尘之妄
“竖子安敢!“
(拍案惊起殿外宿鸟)
“朕的承乾即便瘸足,也是要踏碎高昌城门的!“
(抽剑削落屏风突厥贡品清单)
“武德九年渭水之盟的屈辱,朕用颉利的胡旋舞洗刷干净了——如今倒要送皇子去学那蛮帐礼仪?“
二、斥编剧愚顽
(冷笑掷破《突厥传》)
“写戏文的莫不是没读过《贞观政要》?“
(示房玄龄展开《李卫公问对》)
“药师灭东突厥用的马槊,尔等偏要改成绣花针!“
(忽以弓弦勒紧剧本)
“朕若真要和亲,嫁的也是陌刀阵与明光铠!“
三、定天家铁律
(蘸朱砂圈改剧本)
“听真:“
(笔锋劈开阴山山脉)
“朕的皇子当如青骓踏燕,岂能做毡帐里的金丝雀?“
(掷砚台压住“和亲“二字)
“传旨秦王府旧部——“
(甲声如雷中混着马嘶)
“凡剧中突厥营地,皆给朕换成李靖的受降城!“
四、笑问草原王
(忽展颜,抛三箭于阶下)
“尔等既要演这荒唐戏——“
(箭镞分别刻着“定襄““阴山““铁山“)
“且看这三支穿云箭,够不够换你们可汗跳支拓枝舞?“
(拾起剧本塞进箭囊)
“告诉蛮子:朕在九成宫温着酒,等他带着剧本首级来暖席!“
天可汗世民
(殿外忽起北风,卷着当年渭水的冰碴扑灭烛火)
天策府注疏承乾足疾:李承乾确有跛足,但李世民仍寄予厚望,非剧中懦弱形象
颉利献舞:630年东突厥灭亡后,颉利可汗在长安宴席被迫起舞
李靖三箭:暗指629-630年灭东突厥三大战役(定襄夜袭、阴山决战、铁山受降)
陌刀明光铠:唐军精锐标配,象征李世民“以战止和“的边疆政策影视勘谬令
凡有损天家威严者
当以《秦王破阵乐》震其耳
以《大唐西域记》正其心
演员披玄甲诵《帝范》
编剧跪临渭水摹《温彦博盟碑》——录自《贞观礼乐刑宪》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