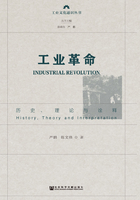
三 阿什顿的《工业革命(1760~1830)》
与芒图和克拉潘的专著不同,阿什顿撰于1948年的《工业革命(1760~1830)》(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这并不妨碍该书成为经典名著。
以一种颇为俗套的方式,阿什顿开篇即写道:“在乔治三世和他的儿子威廉四世治下的短暂时间里,英格兰的面貌改变了。”他列举了这种改变的一系列表现,然后引出了对于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总体观点:“这一系列变化是否能被称为‘工业革命’或许会长期辩论下去。这些变化并不只是‘工业的’,也是社会的与思想的。‘革命’一词暗示了一场突变,事实上,这并非经济进程的特点。那种有时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由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体系,在1760年之前早就诞生了,到1830年之后很久才得到充分发展:忽视历史延续性的本质性事实是危险的。但‘工业革命’一词久为史家习用,并在公共演说中被热情地拥抱,以至于为该词找替代品未免太书呆子气。”[38]可以说,阿什顿清楚地认识到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存在学理上的争议性,但从思想交流的角度出发,他现实地采纳了这个已经广为接受的词,同时指出1760~1830年英国的变革并不局限于工业。
在导论部分,阿什顿简单勾勒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若干基本变化及其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于资本积累的重要性:“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劳动力、土地和资本不断增长的供给必须加以协调。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充满企业家,能快速地组合生产要素,渴望发现新市场,善于接纳新观念。”[39]对资本的正面评价是阿什顿的鲜明特色。而他的观念源自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正统经济学,这与他的前辈汤因比可谓截然相反。阿什顿写道:“不断增长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相结合的供给,使工业扩张成为可能;煤和蒸汽机保证了大规模制造业的燃料与动力;低利率、上涨的物价和对于利润的高预期值提供了投资的刺激。但在这些物质与经济因素背后及其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与国外的贸易拓宽了人们对于世界的视野,并科学化了他们关于宇宙的概念:工业革命同样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如果工业革命被认为是理解与控制自然的进步,那么,它同样是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新态度的开端。在这里,再一次的,从苏格兰,尤其从格拉斯哥大学,最明亮的光射了出来。”[40]亚当·斯密正是来自格拉斯哥大学。换言之,阿什顿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亚当·斯密所代表的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是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方案。因此,《工业革命(1760~1830)》在本质上与汤因比关于工业革命的讲座是一致的,旨在通过探究历史来反思现实,只不过,两者的思路是对立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工业革命(1760~1830)》所具有的利于传播的篇幅与文风了。在写完导论后,阿什顿讨论了工业的早期形式、技术发明、资本与劳动力、“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以及经济变迁的进程。这样的架构,并非关于工业革命的编年史,尽管阿什顿尽可能地描述了工业革命的要点。这本小册子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对于工业革命史实的呈现,而是阿什顿的各种观点。例如,他认为对于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学者们会理想化其劳动条件,这是危险的:“值得怀疑的是制造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对于一个工人来说是否真的快乐,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手受限于生产粗糙类型的产品,变得粗糙而多瘤——在纺织业中尤其如此。确实,大多数工人享受工具和器械,这属于他们自己的乐趣。但是,购置夹子和铲子,砧子和锤子,或者锯子和锉子,通常会负债。在农舍手工业中,当主要的家具就是一架织机或一架编织机,当空气中充满绒毛和灰尘,或者当木炭炉子用来梳羊毛和其他操作而冒烟时,是毫无舒适可言的。”[41]此处,阿什顿解构了一些学者对于前工业时代制造业田园牧歌式的浪漫化想象,暗示了向后看无助于解决当代社会的问题。
对于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生这一众多学者探讨的问题,阿什顿给出的答案是:“一些早期发明因为设想不完善而失败,另一些因为缺乏合适的材料,或者因为缺乏训练有素的工人,或者因为社会抵制变化。工业不得不等待数量足够多、价格足够低的资本去打造‘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桥梁、港口、船坞、运河、水道,等等——这些是大型制造业社区兴起的先决条件。工业还必须等待进步的观念——作为一种起作用的社会理念和行为——从少数人的头脑中扩散开去。”[42]阿什顿再一次提到了观念。而在介绍瓦特时,阿什顿强调了这位发明家在大学里与学者进行过长达数月的深入交流,然后在1765年一个周日的下午灵感突现。[43]与克拉潘相仿,阿什顿看到了工业革命的渐变性:“脑海中必须记住的是,技术发明只发生于国民经济的一小部分领域中:它的覆盖范围只略微超出涉及器械和中间产品如纱和布的工业……各种为满足大宗消费的贸易(除了陶器贸易外)并未立即受到影响。1830年,在英国相当多的农村和城镇里,人们的生活还与一百年前甚至更早的时代毫无两样。”[44]因此,可以认为,对于1760~1830年的狭义工业革命时期,阿什顿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克拉潘所代表的渐变叙事,但他同时看到了工业革命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最终呈现的革命性。进一步说,阿什顿认为工业革命是一种普遍发生的经济现象,而非一次性的历史事件。阿什顿写道:“工业革命应该被看作一种运动,而非一个时代。不管它在1760年后的英格兰、1870年后的美利坚和德意志,还是我们今天时代的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如何表现,它的特质与影响是基本一致的。”[45]这是经济学家透过现象看到的本质。
事实上,尽管工业革命最为炫目的变革来自技术领域,但阿什顿更看重工业革命的经济性质。他称:“工业革命是技术事件,同时也是经济事件:它所包含的资源集聚与分配的一系列变革,不亚于这些资源被直接用于特殊目的之方法。这两种运动其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发明,工业或许会继续缓慢地进步——公司变大、贸易扩展、劳动分工细化、交通和金融更加专业与高效——但那就不会有工业的革命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新的经济资源,发明将很难被创造出来,或者只能被应用于极其有限的领域内。”[46]此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指的就是资本。阿什顿勾画了工业革命前英国资本市场与金融体系的发育过程,分析了工业企业家的各种融资渠道。他认为,在工业革命初期,银行所起的作用不大,最典型的纺织业和冶金业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融资:“他将所赚到的钱最大限度地又投入他的生意中,并不考虑多少立即的回报。”[47]他将一个叫沃尔克斯(Samuel Walkers)的企业家的日记作为例证写道:“一家又一家公司的记录讲述了与沃尔克斯相同的故事:公司所有者同意付给自己很少的报酬,严格限制他们家庭的开支,把他们的利润投入再生产。通过这一方式,韦奇伍德、科特、格拉斯夏、牛顿·钱伯斯公司,还有其他的企业,建立了自己的伟业。”[48]阿什顿塑造了一个勤奋节俭企业家的形象,其隐含的社会道德意义不言而喻。对于与资本具有对应关系的劳动者的境遇,阿什顿认为,工业革命并非像汤因比等早期作者描述的那样漆黑一片:“与广为流传的印象相反,1760~1830年见证了对于人类尤其是年轻人不幸福状态不断增长的关切,甚至对棉业工人也是如此。”[49]他认为工业革命实际上增加了英国的物资供给,通过工业品的出口,大众能够消费更多的进口糖、谷物、咖啡和茶。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工业革命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50]这一观点,与汤因比等人针锋相对。
于是,在全书的最后,阿什顿为工业革命进行了辩护:“一位历史学家曾写下‘工业革命的灾难’这样的语句。如果他是指1760~1830年间英格兰因为战争而导致的黑暗或因为死亡而招致的不幸,这么说无可厚非。但如果他的意思是说技术和经济变迁本身就是灾难之源,其观点则大谬不然。那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早先时代产生的数量过剩的一代孩童吃饱、穿暖并得到雇佣。爱尔兰面对着同样的问题。由于解决问题失败,爱尔兰因为移民、饥荒和疾病,损失了她五分之一的40岁壮年人口。如果英格兰继续作为一个农夫和工匠的国家而存在,她亦难逃同样的命运,就最好的结果看,不断增长的人口重负亦将压垮她精神的源泉。她逃脱了,不是靠她的统治者,而是靠她那些为了自己的狭隘利益而使用新设备进行生产、采用新方法管理工业的人。”[51]这是对工业革命至高的礼赞。作为对比,阿什顿还写道:“今天,在印度平原和中国,男男女女们忍受着瘟疫和饥饿,他们的生活看起来其实比牲畜好不到哪里去,白天他们拼命干活,晚上则挤在一起睡觉。在这些没有经历工业革命而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的国家,大多数人就过着这种亚洲式的生活,体验着这种体力劳动的痛苦。”[52]这段话当然显示出阿什顿身为一个西方人的傲慢,但工业革命作为决定国家发达与否的力量,却是毋庸置疑的。
与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文风平实不同,阿什顿的《工业革命(1760~1830)》字里行间充斥着浓浓的论战气息,尽管他从未明确地指出其论战对手是谁,但倘若熟知相关学术背景,则一望即知。客观地说,由于工业革命这个概念的早期传播过程实际上是对工业革命的批判过程,阿什顿为工业革命的辩护起到了纠偏作用。固然,《工业革命(1760~1830)》是一本具有通俗读物色彩的小册子,在注释和论证等学术规范上十分单薄,但作为职业经济史家,阿什顿的流畅论述还是展现了其深厚的学养,并且从诸如引用企业家日记等内容看得出其对原始史料之熟稔。因此,《工业革命(1760~1830)》是当之无愧的经典。不过,必须指出的是,阿什顿的辩护,实际上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视为一体了,而他对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崇亦有过度之嫌,故《工业革命(1760~1830)》更适合被视为史论,其思想价值要远高于史学价值。